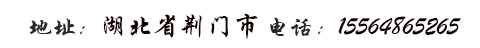春的呼唤
|
北京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http://pf.39.net/bdfyy/index.html 李登建老师题字 春的呼唤 文/田野 一直以来,我似乎对春天有着某种特别的执念,童年荡漾在春日的花海,少年最爱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中年的每一个春天里也常常在门前的海棠树下流连。因我出生在春天,最初的乳名也是“春”字。如此固执的偏爱,好像一种别样的浪漫——“春”以它不可替代的美好向我召唤,我也如约而至的呼唤生命中每一个春一般的存在。 我的第一个春天是姥娘,她叫马秀英,是年出生的,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人,她给了我一个春天、桃花、阳光和所有自由自在生长的世界。在我还没有断奶的时候,就被抱到了姥娘的炕席上,一待就是七年,直到要上小学了,才不得不离开姥娘和她生活的这片土地。 我想要写写她的模样,可记忆中却只有个模糊的影子。姥娘去世那年我已十岁了,像我这样还算挺聪明的孩子,却记不得身边亲近之人的模样,好像很不应当,连我自己都一直不解。现在想来,就是因为姥娘在我的生命中太为重要,像是镌刻在生命中一样,当她走掉时,就将和她在一起的那块记忆整个拿掉了,以至于后来怎么也想不起来。这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大概就是心理学上说的选择性失忆。 后来我问了小姨和母亲等人才还原了姥娘的样子。她们说姥娘是中等身材,四方脸,长得很端庄。她性格耿直,从不拐弯抹角,做事也是干净、利索。听着她们这么说,我的记忆也像是被驯化般的,模糊之中,觉得大约就该是这样的吧。 很多年后的一夜,我毫无征兆地突然做了个梦:旷野之上有座楼,周围一片漆黑,其中一间有光,像是个空的楼,我踩着楼梯上去,门开着,发现姥娘竟然住在这里,原来她一直就住在这个城市。我问她这么多年去了哪里,怎么不告诉我,别人为什么都瞒着我,她为什么不找我……一连串的疑问。姥娘好像没说话,只是看起来她过得不错。我很懊恼,这么多年我怎么就不知道姥娘住在这里,没有给她来送点好吃的,让她知道我已经长大结婚、生儿育女。总之,我像是被一种失而复得的感觉砸晕了一样,即惊喜,又遗憾,还愧疚,五味杂陈交织在胸口。时间紧迫,我得走了,我拼命想要记住这个地方,好下回再来。可是醒了之后,我还是忘了。 这是她走后,我唯一梦到过她的一次。姥娘于我就像是一整个春天,我在梦里呼唤,试图唤回那种遥远的幸福,但梦的短暂又让我有种无能为力的失落感,我只好朝花夕拾、回溯往事。 姥娘家住在山东桓台陈斜这样一个小村子里。进了村子走不远,就有一条胡同,第二个大门就是姥娘的家。 姥娘家那个院子,最南边是一口水井,周围都是树;西南角上的猪圈里养了两头终日无聊的大肥猪;北边是几间大北屋,屋里房梁上有筑巢的燕子。春天里前门的桃树下,我俩坐在那里,姥娘做针线活,我就像小猫一样依偎着她。树上密密匝匝开满了桃花,透过枝条的缝隙看着湛蓝纯净的天空,太阳晒得到处热熏熏的,也暖得我和在树下溜溜达达的小鸡都倦倦的。夏天里下了大雨,开着门望着院子里哗哗的雨砸在地上,砸出一个一个的大水泡,我光着脚丫子跑出去踩上一脚脖泥巴;秋天里姥娘去赶集了,让我在家等着,问我想要啥好吃的,我想不出来,姥娘逗我说:“那就给你买个‘仰天脖’吧。”我一个人在院子里围着槐树、香椿树溜溜达达,仰着脖子望着天,幻想着“仰天脖”的美味,享受着秋天的天高云淡;冬天里,烧了热炕,我脱得光溜溜躺在炕头上热被窝里,听着老人们聊天,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不知不觉进入甜美的梦乡…… 我像小鸟一样飞翔,像风一样自由,像桃树的花苞一样憋着劲,鼓胀着小小的生命,和小伙伴下地割草,在田里摘着野花、吃着浆果,百般聊赖地追鸡撵鹅,将那一段童年的时光活成了天籁。因为她给予我的就是春天般的暖暖日光、冬日里热乎乎的炕头,乃至于我丝毫感受不到姥娘的艰辛。 姥娘摇着吱吱呦呦的纺车纺线,缝补浆洗。穿针是我的拿手戏,将一根粗针穿上线,跑到村口的大杨树下面,将落叶一片一片地穿在线上。我非常努力地干着,想着能为姥娘烧饭时多添一点柴火。 姥娘下地干活,我就和小伙伴一起去坡里挖野菜,最多的是青青菜。姥娘家最常喝的就是棒子面熬的粘粥,开了锅放上洗好的青青菜,一碗黄灿灿的粥,上面漂着碧绿的青青菜。就着姥娘腌的咸菜,和收工回来的姨和舅们,一大家子坐在院子的月明地下,那一顿晚饭是一辈子幸福的回忆啊。 时光就是条溜溜滑的小鱼,不等你抓紧,它就从你手里溜走了。转眼夏天到了,我该上学了,春天就要过去了。 好在,每年秋收完后农活不忙了,姥娘准会来我家住上一个冬天。我放学回家抖落一身飞雪,桌上总有热腾腾的饭菜。晚上围着小火炉,姥娘做点针线,我就在一旁写作业。有一天,我早上起得晚了,慌慌忙忙来不及吃早饭,背了书包就去上学。坐在课桌前肚子里空空的,眼见着窗前由远及近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会儿老师就叫我出去,姥娘从衣服里拿出用体温暖着的一块红薯。我一直不知道,不识字也不熟悉这个城市的姥娘,怎么能找到我的学校?还找到了我在哪个班。反正只要姥娘在,就感受不到严冬的寒冷,我的世界总是热呼呼的。 花开花会谢,月圆就有缺。我不知道命运到底是个啥东西,它就像看不得我好似的,这样美得像抹了蜜的日子过了没几年,姥娘就病了。这年她61岁。她的六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不再为生活的窘迫所困扰,家里的粮囤也总是满满的,日子越来越好。可她这一躺下,就再也没起来。 医院时像个小傻瓜一样围着她的病床蹦来跳去,姥娘给我吃的桃子罐头特别好吃,我问姥娘为啥不吃,她躺在床上看着我说:“你吃,你吃。”别的就什么也记不得了。 没过多久,人就不行了,提前三天拉回了桓台。 她走得很干净,临了也并没有滔滔不绝种种牵挂,好像从毛衣到短袖永远相隔不过几天,春夏的交替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我那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大北屋里,南北朝向放着姥娘的棺材。梁上的燕子窝里叽叽喳喳的小燕子还在,满屋子人影晃动不断,我依旧围着姥娘从小搂着我睡觉的土炕,院里屋里的跑来跑去,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姥娘到底是怎么了,也没有人顾得上搭理我。记不得谁告诉我,要磕头要哭的,人影依旧晃动,很多人都在哭,可我不哭。我甚至还想使我的小把戏,想着在脸上蘸点唾沫,蒙混着迎合大人们悲伤的气氛。 但我理解不了什么是死亡,心里一直想着到了冬天,姥娘一定还会来的! 再一次回姥娘家,一进大门就是那面破旧了的画着松鹤延年的影背墙,我还是照例飞奔着朝着南屋跑去,边跑边喊:“姥娘,姥娘!”可是没有应声,只有姥爷那佝偻消瘦的身影走出来。空荡荡的大屋、空荡荡的心,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姥娘真的不在了,我再也不能一进门喊着就能听到她那熟悉的应声了。没有了姥娘,那个温暖的老房子就只是个房子了,再也不是家了。 这样无数次地回去,无数次地找不到姥娘,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算死了心。打那时起,上学时的路上,也不知怎的,心里就像是有只手抓往外拽一样,我试图对妈说说是个什么个滋味,可怎么也表达不出来,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就是心里难受,我想姥娘了。 姥娘走后的许多年,我近乎偏执地喜欢芙蓉花瓣、青草气味、茉莉花香、泥土芬芳。每一个春的符号都让我或多或少地摸索到些许姥娘曾经给予我的幸福感。而时光流转,我的一次次呼唤仿佛石沉大海,令人伤感。 “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城南旧事》中的英子开始自己学着长大了。姥娘带走了她为我打造的春天,我为此失落的呼唤了春天许久。那个重逢的梦,尽管醒来依旧记不清姥娘的模样,但我释然了,姥娘其实一直都在,她告诉我何谓美好,告诉我珍惜春天,于是我得以到如今这个年纪,还保留着这样一双看得见山花海树的眼睛,嗅得到桂馥兰香的鼻子,还有对一切美好倍于常人的捕捉和感受。 姥娘走了,我还活在春天里。 作者简介 田野,滨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一个普通的人,想要写一写生命中普通的生活,普通的人和事。 往期回顾. 父亲的扶桑花 《渤海文学》编辑部 顾问:李一鸣丁建元李登建 主编:风扬子 编辑:文蔓玉清 投稿须知 投稿邮箱: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usanghuae.com/fshsltx/11543.html
- 上一篇文章: 献给那些喜爱养花却又养不好的朋友们各种
- 下一篇文章: 渤海文学五月精彩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