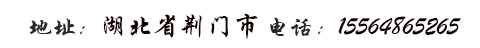夏天,在森林散步才是正经事
|
永恒的躁动,永远的路标 大家好,我是小吃,但是最近减肥健身就不乱吃了,最近大家都放假了,炎炎夏日,都想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凉爽。 而在没有空调的那些年带过我们凉爽地方,森林深处绝对算一处,天然的空调房。但是森林对于日本来说就意义非凡,日本宗教认为森林是死生轮回的道场,有些日本人会认为森林是逃避现实的栖息地,从而使得森林文化成为了日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算是除了樱花外同样重要的图腾。 “物语”的本义,原指讲述“物”的口传文艺。其中之“物”,最早指的是古代信仰中的灵物,即本氏族所祭祀的神以外的神,后扩大到动植物、山川、河流等但凡寄寓有祖灵崇拜意义的自然物。物语是日本古典文艺的典型形态。对于日本来说,电影艺术是现代西方舶来品,可是,善于吸收与创化的日本人很快掌y握了以镜语表达自身的方式,并以之复苏“物语”的原初涵义,赓续本民族的精神信仰与文化传统。 我且将日本电影中这种独特的表意方式名之为“森林物语”。这些电影包括小津安二郎以季节命名的几乎全部作品,沟口健二的《残菊物语》、《雨月物语》,黑泽明的《梦》、《八月狂想曲》,今村昌平的《鳗鱼》、《日本昆虫记》,宫崎骏的《风之谷》、《悬崖上的金鱼姬》,北野武的《花火》、《菊次郎的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河濑直美的《殡之森》、《沙罗双树》,是枝裕和的《幻之光》、《步伐不停》,岩井俊二的《情书》,泷田洋二郎的《入殓师》等等。这些影片讲述或呈现“森林”(动物、植物、山川、河流等)的物语形态或有轻重与多寡、前景与背景之别,但在集体记忆与民族根性上却有着深层、自觉的趋同。 日本学大家梅原猛在《森林思想——日本文化的原点》一书中曾说:“如果有人要问日本最值得夸耀的是什么,我认为值得夸耀的是日本的森林。日本国土上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七,而且这些森林中的百分之五十四是天然林。在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保留下这么多森林。”日本是一个幅员狭窄的岛国,自古以来耕地少,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频发,生存环境极为恶劣,而唯一能够提供丰厚物产的就是广袤的森林。 森林对于日本人的生活实践和精神文化影响深巨,他们的先祖也被称之为“森林之民”。生存本能和对森林强大生命力、物产能力的敬畏与感恩,天然孕育出日本人迥异于西方的类宗教信仰。与西方国家自然对抗型、主客二分论的“草原哲学”相反,“东方国家是自然恩惠富裕的‘森林之地’,自然环境多样、美丽。从这一富裕的自然环境(森林生态系)中,酝酿出人类与自然亲和、人类与自然共生的‘森林哲学’,即自然亲和型、自然共生型自然观或物心一元论型自然观。 以此为背景,在东方,滋生出‘森林宗教’,即自然亲和型、自然共生型宗教或物心一元论型宗教。从而成为‘东方文明’的源流”。并且,与中国、印度等东方农业文明国家相比,日本的这种森林信仰不仅表现尤甚,更构成了日本民族精神结构的核心与支柱。这也就是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所说的,“温润的岛国环境,培育了日本人亲近自然、爱恋人生的温柔细腻的情感。在感觉的洗练方面,别国无可伦比”。概言之,日本文化的源流是森林文化,日本电影的“森林”讲述正是伏根于日本源远流长的森林信仰。 小森林中女主角的精神寄托就是这一片森林 日本的森林信仰与森林文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万物有灵观 万物有灵观是人类初民感知与把握自然事物的普遍方式,典型特点是将外在于己的自然万物生命化、人格化,视其为与人一样具有情感、思想的鲜活生命体。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更是将自己作为森林的一员,周遭的动植物、山川河流和人一样,只是偶然以动植物或山川河流的状貌面世,同自己一样具有生命、灵魂以及生命的互渗互换、生死的轮回罔替。因此,日本人对自然界的生灵总是以礼相待,认为它们是以特别面貌出现且带着礼物(果实、柴薪、皮毛等)来拜访的客人。 正是这种“与物为春”、“万物齐一”、物我不分、天人合一的东方型生命整体观,熔铸出日本人面对万物的谦卑传统,共情地感受自然的恩惠。直到今天,尽管日本的工业文明已极为发达,但日本人这种素朴的感恩之心依然十分强烈。如在电影《风之谷》(宫崎骏,)中,当娜乌西卡看到地下的树根正在慢慢地净化空气,她感叹道:“腐海的产生是为了净化被人类污染的世界,它们把大地的毒素,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面,变成干净的结晶,然后再枯死化为细沙……而虫群们是在保护着这座森林。”由此可以管窥,人与自然的关系虽有从和谐退变为对抗之势,但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并未消蚀日本人森林崇拜的“初心”,依托于广袤森林的地理之利惯常地提挈着他们面对自然的一种敬畏之心和赤子之情。 (二)生命力崇拜 日本人的森林信仰肇始于对巨树生命力的敬畏,继而扩展到森林里一切生命的礼赞。当梅原猛寻访到三棵巨大的古树时,他评论道:“巨树是很了不起的。这些巨树的树龄有三千年,就是说,它们看到了三千年的历史。这样悠久的历史变成巨树的大树瘤,表现为悠然不迫的一枝一叶,我深深地感到它们太伟大了。姿态优美的武雄的巨树,盘根错节的川古的巨树,因遭雷击而伤痕累累的冢崎的巨树——看到这三棵各自具有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历史的巨树,我不禁深深地感动。”接着他又说:“没有任何东西能具有像树木那样巨大的生命力!树木的精灵是生命的象征。因为一颗小小的种子能长成那么高大的巨树,而且可以生存几百年、几千年。再说人是依靠树木的恩惠生活在世界上的。吃的东西是树木提供的,住房、船只、衣服全都是利用树木制造的。所以绳文人利用树木编的绳子在陶器上印上花纹,大概是想把树木的精灵、生命力化为自己所有。” 这就是说,日本人的森林信仰以巨树崇拜为核心,继而树木、万物,巨树是一切生命的核心,而其他的草木、虫鱼、山川、河流等同样以旺盛的生命力获得人们的同情与膜拜。在宫崎骏的动画电影中,这种对生命力的膜拜与礼赞可谓俯拾即是。例如在《幽灵公主》()中,山神被人类割首后,身体慢慢融化,黑色的液体源源不断涌出,覆盖了整个世界,继而幻化出一个鲜花遍地的新世界。《悬崖上的金鱼姬》()中,小金鱼们迎着暴雨大浪飞奔,让人不禁对其强大的生命力啧啧称赞。正是倚借着这种颇具泛神论色彩的森林信仰,日本文艺包括电影艺术方有驰骋自身巨大想象力与表现力的源头活水,并且逐步形成了本民族“物哀”、“闲寂”的美学传统。 《悬崖上的金鱼姬》极具生命力的金鱼姬 (三)植物美学论 万物有灵观和对森林、树木生命力的膜拜,自然导向一种审美层面的“植物美学”。日本民族崇尚生命之美,赞颂生命力充盈之美的审美意识,体现在以植物为审美对象以及植物的形状和姿态所显现的生命力之上。对植物的审美实践不仅成为日本美学范畴的基础,而且成为艺术美的基本精神。植物美学以树木、花草为基本审美对象,注重以直观而纤细的具象寄托人对生命人生的切肤体悟与幽微洞察。 根据今道友信的观察,日本人“审美意识的基本词语中的最重要的概念都是来自植物的。立足于这样的见解来探求表明传统审美意识的术语,就会看到,华丽、艳丽、娇艳、繁盛、苍劲、枯瘦等等,的确大多是从描述植物在四季各大时期的状态而产生并抽象化的概念”。 因此可以说,日本的文化形态是由植物美学支撑的,日本美学的本质是植物美学。仅以“花语”意象为例,电影《步伐不停》(是枝裕和,)中绽放于四月的紫薇花,《扶桑花的女孩》(李相日,)里灿烂如女孩们笑脸的扶桑花,以及《细雪》(市川昆,)、《樱之园》(中原俊,)、《四月物语》(岩井俊二,)等无数影片中绚烂与静美兼具的樱花,无不寄托着日本人对造化自然所恩赐的植物生命的爱恋与礼赞。伴随着季节变换与植物生死的交替,“花语”同时又与“季语”结合,进而孕育出诸如“春”与“樱花”、“秋”与“红叶”这样的对应关系。善感的日本民族正是看中了季节变化所带来的事物形态和色彩的变化,乘物以游心,托物而言志,谨以纤微的植物讲述人对生存、死亡敏感而细腻的感悟。 《扶桑花的女孩》(李相日,)里灿烂如女孩们笑脸的扶桑花 概而言之,日本电影的“森林物语”源于日本传统的森林信仰与森林文化,同时又在美学观念、意象呈现、价值诉求上注入了鲜活的现代意识,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电影的民族性内涵。日本电影这种“以物撄人”、传统和现代兼收并蓄的务实经验,足以为当代中国电影的民族性探索提供重要的智慧启迪。 秉持着“无神论”的我们也应该知晓,一草一木,蠢动含灵。让我们一起在森林漫步吧~ 欢迎登陆西西里岛 这里有最亲切的人,给你讲述最遥远的梦境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usanghuae.com/fshsltx/797.html
- 上一篇文章: 10423期中秋作品杂集
- 下一篇文章: 后篇过什么情人节来看50种常见植物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