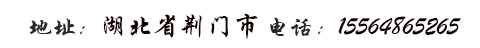好吃不过饺子
|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文|木槿此“饺子”非彼饺子。这是金石荷塘一带的小吃,它沾了“饺子”的名头,却和面粉馅料没有任何关联。它的主要原料是红薯。这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物种在春天被种下,发芽,吸着天地灵气拼命生长,待到初夏雨水丰沛,便被裁剪扦插。像一个脱离母亲怀抱的孩子,被扦插的红薯苗只有以更拼命的姿势向上生长,它在夏日的风雨里,在如火的骄阳里,在慵懒的秋日里,从未停止过生长的步伐。像一个勤恳质朴的农人,一年四季从不停歇。而红薯也果真如农人般不事张扬——单看地面的红薯藤,你是无法知道地下的果实有多少的,非得等到秋意渐浓凉风四起,红薯叶子变红变黄,先将红薯藤割下,一摞摞捆好,然后挥起锄头,才知道地下原来有“黄金”!的确是“黄金”。早年家家户户饲养猪牛鸡鸭,娃娃的学费往往就是圈里那头猪或牛,猪牛胃口大,一餐可以吃一大盆,哪有那么多粮食喂,便是这红薯充当了牲畜的口粮。喂养牲畜的红薯自然是没讲究,拿来做饺子的便大不相同了。红薯收回家后,堆在墙角。祖母或者母亲便用心地挑那些好看的,没有破损的,圆润晶莹的,颜色鲜艳的,多半是那些年俗称的“黄心红薯”,因为这些才够甜够水润。等到挑了一大堆,就放在别处慢慢晾(方言叫“摊”)着。据说是要晾干表面的水分,不然容易腐烂,带着泥巴自然干燥的红薯会保持好自身的营养,然后在寸寸的光阴里慢慢释放自身的甜蜜素,这样才最好吃。晾得不够,红薯太硬太生涩,像未经世事的毛头小子,总是欠点火候;晾得太久,红薯容易腐烂,往往还带着酸腐之气,像圆滑过头的人,有种让人生厌的油腻;只有软硬刚好,用金石荷塘方言是“劳瓜哩”,握在手里不觉得咯手,疲软而不腐烂,有种温柔的顺从,同时又保留有红薯本身的那种红色或者灰棕色,这才是做饺子的上乘材料——农人对于节气和尺度的把握永远如此契合自然而又妙不可言,所谓大道至简,烹食之法,又何尝不是人生哲学。等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闲在家的人们无聊,便说来炸饺子吃吧!对,如果说红薯是这道小吃最主要的原料,炸便是最主要的方法。选几个“劳”得刚刚好的黄心红薯(现在改成用“苹果红薯”了,单这名就挺让人垂涎的),拿掉外面风干成型的泥块,洗净,削皮,切成丝。刀工是一个人厨艺的重要体现,只见左手拿红薯,右手拿刀,手起刀落,咚咚咚咚,三下五除二,眨眼间,一堆整齐又细长的黄白色红薯丝便在案板上排列开来。而让你惊异的不仅是这漂亮的红薯丝,更是那切红薯丝的人居然可以不用看案板边切边和你谈天说地。无须奇怪,多年的主妇熬成大厨,基本上每家的女人都有这功夫。切好了红薯丝,便开始拌了。通常是加米粉,而且一定是自己种的当年的粳米。米粉是先一天已经在石磨上一圈一圈推过来又推过去碾碎的,不是机器碎的,机器碎的没有那种人和石器心灵相通打磨而成的温度和味道。我们也曾试过用糯米,但无奈糯米和成的红薯丝下锅无法成团,也没有粳米的香脆,这也是一个不解之谜,可能一物降一物,糯米只适合做糍粑和雪花丸子吧!粳米粉和红薯丝拌到一起,敲几个鸡蛋,倒入点冷开水(这几年已经进化成纯牛奶了),加点自己磨的红辣椒粉,还可以加姜丝或者葱蒜叶,再依个人喜好加入盐或糖,用戴了手套的手细细拌匀,等到这些东西都浑然一体了,便可开炸了。炸饺子通常是柴火,噼里啪啦,火苗乱窜,烟雾袅袅,那才够味。柴火灶上支一口大锅,里面是黄澄澄的自己榨的茶籽油(也可以是菜籽油)。等到锅里的油开始变热,往往会浮起一层薄薄的白沫,需把那层白沫捞走,不然会影响饺子的味道和色泽。捞干净了白沫,拿起已经和好的红薯丝,无须刻意拿捏成何种形状,就那么随手一扔,“吭哧”一声,炽烈的油遇上冰冷的红薯丝,像天遇到了地,像风遇到了雨,立马就有了故事和永恒。油锅在“滋滋滋滋”地响着,红薯丝在锅里翻滚着,跳跃着,变幻着,之前还白白红红的一团,不到三分五钟分钟便成了金黄,这时候红薯丝的细长秀美便又重新露了出来,成虾状,因而也叫“花公饺”(金石荷塘方言把虾叫成“花公子”)。与此同时,那种甜腻与油炸混合的焦香,也在空中氤氲开来,像记忆中某种醉人的甜,令人幸福得惆怅。嘴馋的小孩多半已经忍不住了,拿起一个便开始吃,多半是被烫得龇牙咧嘴,但他们也是不会放弃吃的。这时候的饺子其实还不是最好吃的,最好的是炸过一遍捞出来沥干油,过一分钟等它稍稍冷却再迅速入锅,这回只一分钟左右便要及时捞出来,太久便会焦。炸过两遍的饺子,那才是真正的美味,又香又酥又脆——红薯的甘甜,米粉的醇厚,辣子的泼辣,生姜的辛猛,葱蒜的鲜香,茶油的浓酽,种种味道,都在其中,有如人生。与别家不同,我的母亲习惯了在第二次炸好的饺子捞出锅后,迅速撒上几把自己种的黑芝麻或者白芝麻,热气腾腾的饺子金黄油亮,芝麻星星点点,煞是好看,吃起来也更香。饺子易润,所以必须密封好。那些年正月里去拜年,家家户户的果盘里总是摆着这种形如虾状的饺子。虽然吃过以后手上会沾有油,滑腻腻的,但总是爱不释手。这几年,每年的高三复习课上总会遇到白居易的《邯郸冬至夜思家》: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伴身。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我总是想,冬至夜阖家团圆吃饺子的时候,白居易孤身一人思绪万千,远离家乡的游子,或者就是长达十几年里,我在岭南大地为生存奔波劳碌顾不上回家过年的父母,应该也是想起家人,想起家中的饺子的吧?我比白居易幸福,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羁旅乡愁,并且在这个年里,我就吃到了母亲现炸的饺子。总有这样的一幅画面,定格成为温暖:柴火灶边,母亲在炸饺子,父亲在添柴火,金黄的饺子在锅里翻滚着,沸腾着,伴着火苗,一起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节欢欣鼓舞;灶边多半环绕着馋嘴的我们,痴痴地盼着,盯着,吃着,怎么吃也吃不腻——那曾经是我们,现在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父母的嗔怪声,我们的说笑声,孩子们的吵闹声,柴火的噼里啪啦声,跳跃在微冷的空气里。柴火房外,雪落无声,四周不时有鞭炮声,就要过年了。作者:木槿,教师。本文系作者投稿,配图均来自网络。木槿文章:1、人间草木风中木槿2、没有春风,哪来春雨 温馨提示: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可查询土著民自创办以来的所有文章乡土文学 生活 记忆第11届中国传媒大会最具活力文化自媒体第12届中国传媒大会最具乡土气息自媒体第13届中国传媒大会最具人文情怀自媒体扎根乡土留住乡音传递乡情守住乡愁合作/投稿:toozoom 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usanghuae.com/fshsltx/8304.html
- 上一篇文章: 年12生肖全年婚姻财运事业运势
- 下一篇文章: 好文书亭叶君官方认证热门小说精彩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