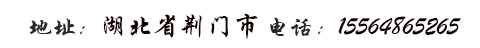花名十样锦
|
大诗人刘禹锡的那首《乌衣巷》很出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在夫子庙朱雀桥的对岸,撞见蓝底白字的“乌衣巷”的门牌,绕进去,当年第一次来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个体饭铺子,如今已是粉饰一新的“王谢故居”,里面有一座小楼,叫做“来燕堂”。自然,并没有旧时燕子来探故人。看起来好像万事俱备,唯欠桥边一丛野草花。可是哪有什么野草花,出现在市声鼎沸的夫子庙而毫不违和?谁真要在朱雀桥边栽上花,恐怕也是驯化了的,文人格调或小资情调的吧。然而我心目中,却有一种草花,可以入刘禹锡的这首诗。它不完全是野花,性情却“贱”得很,门前屋后的几个破旧的瓦盆、罐子,或者菜园地头的一片弃地,春末撒上一些种子,夏秋之际就蔚然一片繁花似锦。我初次见它还是在高淳老街,阒静无人的深巷,初秋的阳光在青砖墙上斜切出明暗的段落,为墙根的绿苔保留了一片领地,头顶悬挂的衫裤在风中招展,黑漆的木门倚靠着坐在小椅子上手摇羽扇的白发老妪,当时我触手所及的就是檐下的数盆草花,而最常见的正是这种当地人叫“十样锦”的。后来,又是同在高淳的漆桥古村,当我走进青石板街的里巷深处,一位热情的老人拉我进他家初建于元代的祖屋参观,听说我是教育工作者,又敲开失去双亲的孙子的房门,满怀期待地叮咛我和他孙子说上几句。我全部照办了。但是不知道这究竟有没有用处,毕竟他孙子已经是个半大小伙的住校高中生了。在那条僻静无人的隘巷,五颜六色的十样锦开得十分热烈。我喜欢这种花,倒不是因为它颜色多,虽说它的名字应该就是由此来。这花花期很长,我现在生活的句容山中某书院的林间隙地、路边、台阶下随处可见的芊绵的什锦花,从六月末能开到十月之后,直到霜降时节,叶子萎黄了,花头也早已枯槁了,依旧在寒风中挺立,简直是一支一支雕塑般的天然干花。什锦花大概也是菊一科的,“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不过它和菊花这个高士终究还是比不来。第一个它没有菊花沁人的香气,花瓣也不像菊花那样有种种瑰奇的造型和清雅的色泽。单看一株花,它够单调。花瓣只有单色,多是单瓣,至多是两重花瓣,像婴儿的手指一样,这又让我联想到雏菊了。它粗短的茎也几乎是直的,一点也不窈窕,正如它的叶子也是浑朴的水滴形,而不像菊叶的羽拂纷披,或兰草的疏密有致。可是它一开就是只一朵花,一门心思地开一朵。一朵是嫣红还是绛紫,是单瓣还是重瓣,它并不在意;是开在篱笆旁还是花盆里,也不重要;是形单影只还是淹没于一片花海,它都不管。它只管老老实实地开好这朵花,从圆茁的花苞,到初绽的蓓蕾,再到舒展开的红的、白的、紫的、黄的、粉的一圈花瓣,然后就是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褪色,直到在凄风苦雨后变成木雕的灰色。“花褪残红青杏小”,这是苏东坡伤春的词句。然而我独赏秋深的十样锦“花褪残红”的寂寞。就像我早年间,对父亲非要买那种叫“万年红”的对联纸,感到有些迟疑,因为我觉得一年下来,风吹日晒雨淋后的门联的红纸,像史铁生笔下的地坛一样,褪去了炫耀的朱红,午后的阳光照在那泛白的纸上,有一种水落石出、风霜高洁的素朴和笃定。或许,是我自己的心境有些过早地感到寂寞吧。“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我并没有“多少蓬莱旧事”值得回首,却似乎颇能体味一朵花的寂寞。十年前在万里之外的桂林负笈求学,师大育才校区一处只容两人擦肩而过的捷径,拐角的花坛里有一株扶桑花(又名朱槿),我是几年后才知道它的名字的,它单瓣的红花,在雨后更显娇艳,可是匆匆过客除了我,似乎没有人在意它的存在。我的寂寞是因为感同身受这种类似于放废的处境,还是与唐朝名相、广东人张九龄“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旨趣相契,我可说不来。但是,我知道一点,十样锦是从来没有寂寞过的。元稹诗中古行宫的牡丹,师大沦为“路人甲”的扶桑花也没有,朱雀桥边的野草花更不可能。本文封面及插图的什锦花照片,来自于网友素面彝女的新浪博客,特此致谢!無華菓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usanghuae.com/fshxgpw/9674.html
- 上一篇文章: 完结新文明桂载酒扶桑知我桑沃超高收藏
- 下一篇文章: 这4种花的名字土掉渣,开出的花却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