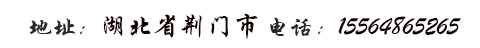天下草木更重情
|
没有花,没有草,就没有世界。语出《佛典》的“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话还是值得深深玩味的。我在读《东方草木之美》前并不知道西莉亚·费希尔为何许人也,只是对书名感兴趣,于是便静下心来读。 关于西莉亚·费希尔的信息我知道的很少,只知道她“拥有伦敦大学科陶德艺术学院硕士与博士学位”,曾经出版《植物大发现:黄金时代的花卉图谱》《鸟的魔力》《中世纪花卉手册》《文艺复兴时期的花卉》等著作。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西莉亚·费希尔是研究自然科学的,而且致力于花卉研究,但我看过《东方草木之美》以后,却不得不折服于她深厚的文学功底,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功底,谈起古典诗词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她在勾魂摄魄、洋洋万余言的引子《花园的历史》中说起孔子,说起白居易,说起曹雪芹。我觉得她所说的孔子、白居易,曹雪芹和我们所知道的孔子、屈原、白居易,曹雪芹还是有些不同,而这不同正是她的视角。 人们大都知道孔子,但未必知道《论语》里有关于杏花的描述和记载,而西莉亚·费希尔不仅在《论语》中看到开放的“杏花”,似乎还听到孔子在杏坛讲学的朗朗之声;埃兹拉·庞德是美国后期象征主义诗歌的领军人物,对中国古典诗歌和日本俳句都有研究。他在文学巨著《诗章》中假借孔子之口吟出“这杏树盛开的花朵/从东方飘到西方”的优美诗句。我是读过《楚辞》的,读的马虎而笼统,西莉亚·费希尔却说“中国古典文集《楚辞》确立了诗咏植物的文学传统”,这种评论屈老夫子应该高兴吧?说到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我们大都知道他的《长恨歌》《琵琶行》《卖炭翁》这些一唱三叠的千古名篇,但有多少人知道白居易的《买花》,反正我是不知道的。或许西莉亚·费希尔是出于研究花卉的需要,才把香山居士的《买花》翻检出来,这是没有答案的悬念。诗中写道:“共道牡丹时,相随去买花。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香山居士在西安牡丹花市看到的是买花的贵胄和看花的农夫。贵胄挥金如土,一株百朵牡丹出价八万,而这八万重金的实际出资者则是发出“长叹”的千千万万个农夫。诗风一如《卖炭翁》对贵胄给予鞭笞和嘲讽,对劳动人民则给予无限同情。 刚写道的这些,肯定是西莉亚·费希尔所“迷不悟”的,但做为一个西方学者,在香山居士留下的多首诗中能把《买花》找出来并融入自己的研究当中,应该是难能可贵的了! 西莉亚·费希尔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更是情有独钟,她认为《红楼梦》是描述中式园林建筑的典范,而曹雪芹“描绘的园林位于南京”,如果不是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有深入研究的学者是不可能得出曹雪芹“描绘的园林位于南京”这样的结论的。西莉亚·费希尔同时指出,《红楼梦》中“对于‘南京瓷塔’的刻画对18世纪欧洲流行起来的东洋风情产生了重大影响”。南京瓷塔确有其建筑,但在《红楼梦》我没有找到关于南京瓷塔的描述,就此我还请教过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孙兰廷,先生对《红楼梦》颇有研究,他说也没在《红楼梦》中见过“南京瓷塔”。综合分析西莉亚·费希尔所说“南京瓷塔”似指明成祖朱棣为纪念其生母贡妃而建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据资料记载,建这座高达80米的大报恩寺琉璃宝塔费时20多年、耗银万多两,通体用琉璃烧制,塔内外置长明灯盏,因约翰·尼霍夫把它写进游记和安徒生把它写进童话而誉满欧洲,被当时西方人视为代表中国的标志性建筑,有“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之誉,被称为“天下第一塔”。但“南京瓷塔”并没有在《红楼梦》中“通体发光”! 西莉亚·费希尔对威廉·钱伯斯推崇倍至,她说“年,威廉·钱伯斯勋爵出版的《中国房屋设计》引领了中式园林在英国的风潮”。 威廉·钱伯斯是英国乔治时期最负盛名的建筑师,曾写过《中国园林的艺术布局》《东方造园泛论》等书,对中国园林倍加赞赏,他主持在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建造的中国塔在欧洲引起极大轰动,而威廉·钱伯斯的构思和设计是否受到“南京瓷塔”的影响不得而知。 西莉亚·费希尔的《东方草木之美》主要是讨论“绽放在西方的73种亚洲植物”。这些植物大都是中国“移民”,即便不是中国“移民”,也与中国有着某些干系。每种植物都配有绘画和解说,我钦敬和惊叹西莉亚·费希尔的解读文字,每种植物的解读文字都在千字以内,除清晰地介绍原产地和“走进”欧洲的时间外,还会涉及历史、风俗、逸事、人物和诗词。解读文字的凝炼与精粹,饱满与丰盈,令人无限唏嘘。 艾草(艾蒿)是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植物了,因为它和屈原有关、与端午节有关、与何仙姑有关。艾草“移民”欧洲时,何仙姑没有跟去,所以希腊人便把艾草献给女神阿尔忒弥斯,——西方的何仙姑。两千多年前,艾草就是林林总总的中草药大家庭中的成员,西莉亚·费希尔说“当今一种主要的抗疟疾就是由这种植物提炼而来,其中的主要成分青蒿素可以阻断疟原虫从红细胞中摄取营养”。 中国女药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屠呦呦荣获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理由是“她发现了青蒿素,这种药品可以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尽管端午习俗把艾草和屈原“捆绑”在一起,但屈原并不喜欢艾草,他在《离骚》里写道: 户服艾以盈要兮 谓幽兰其不可佩 《竹书纪年》是唯一躲过秦朝大火而保存下来的编年体通史。不仅中国的历史与竹子有关,而且竹子也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的诗里画中。 明朝末年书画家胡正言就特别喜欢竹子,他把自己的居所题为“十竹斋”,胡正言对中国文化史的贡献在于他主编的《十竹斋画谱》采用当时流行的饾版和拱花木刻彩印技术,把中国传统印刷技术推向最高峰。所谓饾版是明末在木刻彩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套印技术;所谓拱花,类似于现代的凹凸印、浮雕印,是一种不着墨的印刷工艺。《东方草木之美》一书中的竹、梅、菊等插图就是选自《十竹斋画谱》。 画竹、写竹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堪称大家,他的《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可谓家喻户晓。然而,西莉亚·费希尔总是不经意间让你耳目一新,但在介绍竹子时并没有引用郑板桥的《竹石》,“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会把你引入另一种意境。 王雪娟是生在成都、长在成都的美女记者,我向她询问成都为什么被称为“锦绣之城”,她居然惊愕地反问“有这种说法”?毕竟是成都人,她接着发挥道:“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因为蜀锦蜀绣。” 不尽然也,西莉亚·费希尔是因为木槿。成都遍植木槿,木槿爬满城墙,随着阳光照射角度的不同,木槿花的颜色也在变化,因此成都被称为“锦绣之城”。西莉亚·费希尔又说木槿就是扶桑,又以徐福的故事带出为什么日本被称为扶桑。然后西莉亚·费希尔又说木槿也是芙蓉,并引唐代老僧寒山的“未必长如此/芙蓉不耐寒”的诗句打趣。然而,懂花的人说木槿、扶桑、芙蓉的颜色、花芯、形状和花期都不尽相同。木槿、扶桑、芙蓉到底是同一种花还是同属于一个家族,我就不得而知了。 寒山的《城中蛾眉女》全诗是这样的: 城中蛾眉女 珠佩何珊珊 鹦鹉花前弄 琵琶月下弹 长歌三月响 短舞万人看 未必长如此 芙蓉不耐寒 李白、李商隐都写过关于牡丹的诗,西莉亚·费希尔在论述牡丹时曾加以引用,她还知道唐玄宗还有个牡丹园。但第一个向欧洲描述牡丹的居然是元代来中国的大旅行家马可·波罗,他把牡丹称为“卷心菜一般大小的玫瑰”。我读过好几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怎么没有看到绽放的“牡丹”啊! 关于牡丹的古诗,我还是喜欢刘禹锡的《赏牡丹》: 庭前芍药妖无格 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 花开时节动京城 桔梗、贝母、百合等都是西莉亚·费希尔在《东方草木之美》一书中提到的中草药。我对药材是情有独钟的,从小学到高中毕业,我的学费基本上是靠自己挖药材换钱解决的,可以说,中草药是我求学的“绿色银行”。虽然已经过去40多年,但孩提时代满山遍野挖药材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我所赖以生存的那个村庄周围的山上能挖到的药材有防风、黄芹、桔梗等,但最多的是百合,一片一片的,开起花来红灿灿的,特别热烈而又妩媚。百合的茎儿是独根儿,一般要高出草地十几厘米,所以绿草地上摇曳着红云般的花朵,那是怎样一种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啊! 我上高中时,为让学生在农村的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学校要分成农机、红医、修理等若干个所谓的专业班,去哪个班学什么专业都是要考虑家庭背景的。我别无选择的被安排到兽医班,即便是学有所成,将来也是和牲畜打交道。但我学的特别认真,师傅是当时公社兽医站的站长,他看我能下功夫去啃《汤头歌》《药性赋》甚至是《本草纲目》这样的医书,认为或许是个可造之材,就让我住在兽医站,要比其它同学多吃一些“偏饭”如果从传统的师道尊严的角度来说,他不是老师而是师傅,我不是学生而是徒弟。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我明白了一些医理,记住了一些药性,而且还学会了劁猪骟马,如果文学一点儿说就是剦割就是去势。毕业时,师傅把他使用几十年的一套劁猪工具行话称“灯笼”送给我,语重心长地说:“回到农村,凭这个也能混碗饭吃了!”然后嘹亮地喊出一嗓子:“劁—猪—喝—哟!”依然是行话,意为只要会劁猪,就能有吃有喝! 扯的有点远,因为谈到《东方草木之美》的中草药,也就信笔涂鸦地写出一段鲜为人知的生活经历,还是尘封起来吧! 西莉亚·费希尔在《东方草木之美》中写树、写花、写草,说到家是在写情,树之情,花之情,草之情,人之情! 中国有句老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句话听了许多年说了许多年也麻木了许多年。读罢《东方草木之美》忽然觉得不对,应该是人有情,草木也有情。 草木有情,人间有爱!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fusanghuae.com/fshrybw/11661.html
- 上一篇文章: 朋友圈刷到这ldquo坐不住rdq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